二战以来德国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特别是 2008—2012年,尽管德国身处美欧金融危机的旋涡中心,但仍然展现了较好的韧性。
德国与中国在经济金融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上存在较多相似性。例如,中德两国金融体系的银行主导特征都十分明显,国有或公共金融机构比重高,两国都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特征明显,两国都实行大陆法系,等等。
从国际比较研究看,德国金融体系非常有特色,很“德国”,讲求秩序感,总体结构稳定、层次分明,演进过程保持了其自身的特色。
同时,德国金融体系成功与失败之处都耐人寻味,可以为探索中国的金融发展道路带来很多启发。
本文选自张晓朴在《金融的谜题》书中的前言《中国金融改革如何借鉴德国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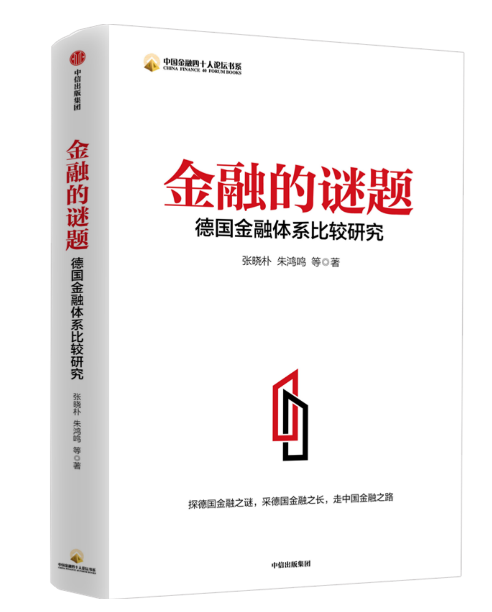
被忽视的德国金融体系
为什么要研究德国金融体系?有四个明确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吸引我开展这项研究。
一是德国较好地处理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作为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长期保持在 20% 以上,制造业占比位居主要发达经济体最高水平,而 2018 年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仅为 3.7%。
二是德国保持了长期的金融稳定。二战以来德国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特别是 2008—2012年尽管德国身处美欧金融危机的旋涡中心,但在这一轮危机中仍然展现了较好的韧性,主流学者和媒体鲜有提及所谓的德国“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020 年德国金融业总体稳定,经济收缩幅度小于欧盟多数成员国。
三是德国与中国在经济金融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上存在较多相似性。例如,中德两国金融体系的银行主导特征都十分明显,国有或公共金融机构比重高,两国都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特征明显,两国都实行大陆法系,等等。
四是国内对英美日的研究较多,对德国金融体系的研究和关注较少。关于德国金融体系的中文文献并不多,不少文献分析性不够,甚至存在事实描述不准确的问题,可能产生误导。
当然,直接驱使我们研究德国金融体系的动因,还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金融体系有能力胜任新的使命吗?如何才能胜任?在金融发展改革监管的过程中,我们如何科学借鉴国际良好实践,英美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模式,哪些可以学,哪些学不了?如何把一国金融发展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大视角下考察,从而得出客观结论?在金融制度演进过程中,需要夯实哪些基础、克服哪些惯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国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所必须回答的。
德国不仅是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也是一个以金融著称且受益于金融的现代化国家。无论是 19 世纪 70 年代实现统一后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是二战后实现“经济奇迹”,都离不开金融的基础性作用。德国经济的成功总是铭刻着德国金融的荣耀。在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中,日德模式也被认为是与英美模式比肩的另一类主要金融体系构建方式,成为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大量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
20 世纪 90 年代后,美国经济强势,经济增速大幅领先其他发达国家。德国、日本却日渐式微,德国意外沦为“欧洲病夫”,日本更是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1990 年,德国、日本经济规模与美国之比分别为 26.8% 和 52.5%,到 2019 年已降至 18.0% 和 24.0%。经济增长绩效的巨大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两种金融模式的价值判断,英美模式越来越被认为是最佳实践,日德模式则出现边缘化迹象。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借鉴样板的转向上,也体现在德国金融体系努力向英美模式转型的尝试中。德国金融体系及其可取之处一度被忽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在美欧独树一帜,人们这才开始重视德国金融体系在避免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控制宏观杠杆率,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良好实践。
除了中国和德国在经济金融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上有较多相似性,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一些恰恰在德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或规避。弄清德国金融体系的基本事实和内在运行逻辑,发掘德国金融体系的可取之处,对中国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大有裨益。
充满谜题的德国金融体系
德国金融体系个性鲜明,谜一般的魅力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化和私有化浪潮,处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德国金融体系却置身事外。回过头来看,德国金融体系的这种特立独行并不是顽固守旧,而是展现了金融功能定位和金融内在结构的稳定性、抗干扰性,这根源于德国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历史传承。
避免了经济金融化的浸染,维持着“小金融、大实体”格局。与美国、英国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趋势性上升而制造业比重大幅下降相反,德国始终维持着较小的金融规模和庞大的制造业部门,金融业比重长期低于 5%,制造业比重则始终高于 20%。在非金融企业的收入结构中,食利性收入份额保持稳定,生产要素“脱实向虚”的现象不突出。
长期保持低杠杆率,形成了发达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大分流”。过去 20 多年来,受金融化浪潮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等发达国家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与此相反,德国宏观杠杆率不升反降,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全球趋势形成了强烈反差。2019 年年底,德国宏观杠杆率仅为 180.6%,不仅低出主要发达国家 70 个百分点以上,甚至还低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隔离于私有化浪潮,保有大量非利润最大化导向的银行。在全球私有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受储蓄银行市政托管体制、联邦主义等因素影响,德国几乎没有出现公共银行(储蓄银行、州立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合作社的私有化,与美国、英国、欧洲其他国家和大多数转轨经济体形成了强烈反差。由于银行业隔离于私有化浪潮,无论是按机构数还是资产规模计算,私营性质的商业银行部门均不占据主导,起主导作用的是非利润最大化导向的银行。与此相关,在公司治理领域,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全球性浪潮在德国的影响也有限。
高度稳定的德国金融体系
德国金融体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稳定,这既体现为金融结构和金融文化的延续性,也体现为难得的长期金融稳健。
银行业长期维持三支柱框架。从历史演进特征看,德国金融体系呈现出了惊人的延续性。自 19 世纪中后期形成商业银行(私人所有的银行)、储蓄银行部门(国有或公共银行)和信用社(合作制银行)的三支柱框架后,德国银行业结构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德国“经济奇迹”、全球私有化浪潮后,依然保持基本稳定,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欧洲许多国家的三支柱框架已经消失。此外,规模较大的政策性银行部门也得以延续。三支柱框架的延续性而非三支柱框架本身,才是德国银行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
金融的亲实体经济属性长期得以保持。我们将德国金融体系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密切互动称为金融的亲实体经济属性。19 世纪后半期,德国金融体系发展出了可以为企业和产业发展提供长期资本的银行体系,成为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关键优势之一。管家银行关系是德国金融亲实体经济属性的集中体现,在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仍广泛存在。在管家银行模式下,银行为企业提供隐性长期融资承诺,承担长期融资提供者、流动性保险提供者和金融救助积极主导者等角色。部分得益于此,德国银行“雨天收伞”的现象并不突出。
金融体系长期保持稳健。二战后,德国并没有像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一样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货币稳定、住房(金融)市场稳定和企业自立是德国金融稳健的三大支撑因素。其中,住房(金融)市场稳定或金融与房地产的良性循环受益于德国央行对货币的保护、发达的住房租赁市场和审慎性住房金融制度。住房金融制度的审慎性集中体现为基于 MLV(抵押贷款价值)的抵押物价值评估、贷款价值比低且以 MLV 为基准计算贷款价值比、固定利率占主导、再融资以不出表的潘德布雷夫抵押债券模式为主。MLV 是对房产价值的保守评估,其评估值通常是经济周期内的最低价格。这些制度设计,有助于隔离货币政策变动对房地产市场的扰动,弱化金融与房地产市场顺周期性叠加,避免房价上涨与房贷扩张的螺旋式循环。
具有启示意义的德国金融体系
德国金融体系并不完美,存在着风险投资和股票市场发展滞后、为未来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同时,德国金融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也与中国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如此,其存在本身就极具启发性,它向我们展示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多样性和大国金融体系的独特性。
德国金融体系至少给予我们十点启示。
一是建设适合国情、适应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德国金融体系 200 多年的独特演进道路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核心在于适合国情和适应发展需要。
二是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再平衡。德国的实践表明,过度金融化和金融业在报酬结构中占优并非历史演进的必然,金融在报酬结构中不占优并不必然影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功能发挥。
三是把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与去杠杆有机结合。德国的实践表明,维持低宏观杠杆率不应只是金融部门的事,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带来的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低杠杆率对于降低宏观杠杆率更为重要。
四是维护金融多样性和竞争秩序。德国的实践表明,金融高效、稳定地服务中小企业的秘诀在于金融的多样性,在于使多样性得以维持的竞争秩序。多样性的结构内含着稳定器机制,可以避免金融机构行为同质化和顺周期性叠加,使金融体系保持韧性。
五是发展关系型融资和耐心资本。德国的实践表明,关系型融资和在此基础上的耐心债务资本是银企关系共济、富有韧性的秘诀所在。德国式关系型融资并未使银行沦为日本式“僵尸银行”,这与德国避免了房地产泡沫、银行重视抵押物、企业自立等因素相关。
六是确保住房金融的稳健发展。德国的实践表明,住房金融具有系统重要性,住房(金融)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石,审慎和节制是住房(金融)市场稳定的关键。
七是完善国有银行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和法治基础。德国的实践表明,公共银行的效益并不一定低,可以成为银行体系的稳定器,但其前提是必须具备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法治保障,必须有效避免政府不当干预。
八是推动企业自立和内源性资本补充。德国的实践再次表明,“只有关注到公司部门,对一国金融系统的探讨才具有完整性”。德国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关系,是金融和企业相向而行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企业自立或重视内源性资本补充所决定的。这种自立性,是企业强劲竞争力和自我约束的统一。
九是一国无法靠货币超发创造繁荣。德国关于货币的正反两方面经历表明,币值稳定对竞争秩序、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极其重要。不能仅仅将货币政策视为进行逆周期调节的短期工具,要更多关注货币政策对竞争秩序的基础性影响。在现代货币理论风头日盛的今天,德国的经验更显得弥足珍贵。
十是有耐心地坚定发展股票市场。德国在股票市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揭示了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前提条件。
当然,德国金融体系的相对保守与稳定,也使其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力不从心,这对于一国技术进步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不得不说是一种致命的缺陷。我们在借鉴其长处的同时,需要认真分析,取其精华。
了解更多
本书是近20年来国内少有的对德国金融体系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德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上存在诸多相似性特征。中德两国金融体系的银行主导特征都十分明显,国有或公共金融机构比重高,两国都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出口导向性特征明显,两国都实行大陆法系等。德国金融体系成败得失都耐人寻味,可以为探索中国的金融发展道路带来很多启发。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各方面研究与讨论德国金融提供一个基础和概念性框架,关于德国金融对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启示,每位读者都有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都会从德国金融体系中受到各种各样的启发。作者期待读者提出自己的建议。

Copyright © 2007-2025 www.nmgxjr.org.c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内蒙古新金融研究院 版权所有
内蒙古新金融研究院 中国网通集团提供宽带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 蒙ICP备18004368号-1
营业执照 技术支持:微邦网络

蒙公网安备 15010302000322号




